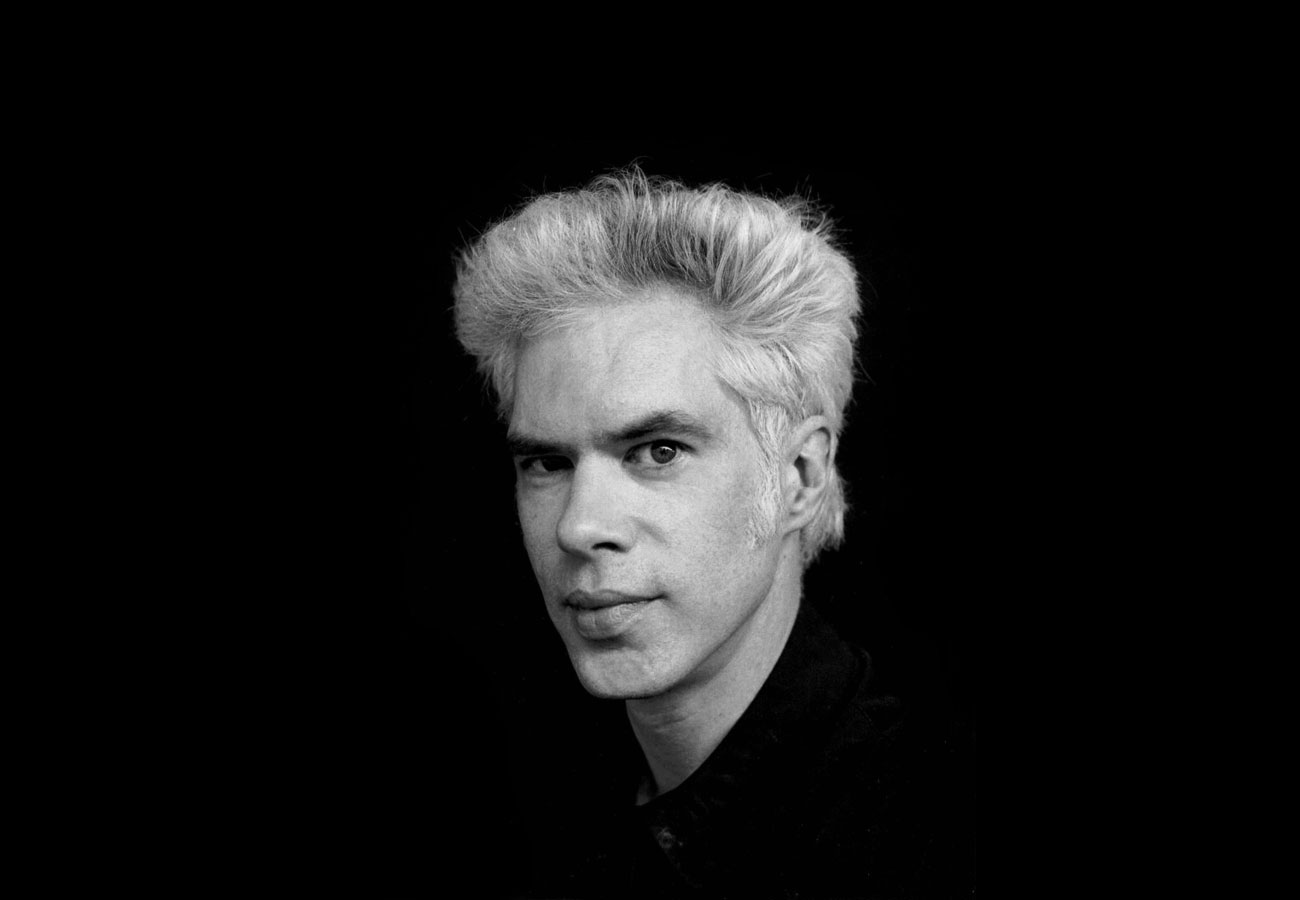已記不清看過幾遍《一一》了。
只記得初次觀賞,是楊德昌離世前後,三小時片長,拼湊著兩次看完。電影結束,像聽完一場交響樂,也彷彿走完一趟人生。幾年前,等不到電影在台灣上映,索性上網買了Criterion Collection發行的藍光DVD,重看了好幾次,像看舊情人的臉書,每次溫習總會發現不同的東西。
如同楊德昌在DVD裡隨片講述過的,他想用最簡單的方式,拍一部講完整個人生的電影,以家庭為形式。片名《一一》,其實就是中文字典裡第一個字,直覺性的讓它重複,就變成「一一」了,合成一個字,就是「人」。而英文片名呢,《A One and A Two》,即是音樂表演中,特別是爵士樂的即興演奏(jam session)之前,樂手低聲嘀咕的開場白。楊德昌在筆記裡寫下,人生如是一首爵士樂調。
《一一》如同一首結構恢宏、敘事精確、細節嚴明,調性溫柔、尖銳、又包容的史詩樂章,娓娓道來,平淡深刻。
最好的日子
電影起始於一場婚禮,結束於一場葬禮,生命起落,日子像浮雲。阿弟口中最好的日子,是他的婚禮,無奈舊情人雲雲不請自來,攪亂一池春水。吳念真飾演的NJ,無意間把阿弟的婚紗照上下顛倒擺放,暗示著這段姻緣的錯置荒謬,也讓我想到楊德昌一向對婚姻的悲觀看法,《青梅竹馬》中,侯孝賢飾演的阿隆說過,「結婚不是萬靈丹。」
也許婚禮背後的真相,更多是為了彌補道德上的責任焦慮,好比上了車後,總得補票。而仿若楊德昌化身的洋洋,背對著鏡頭,看著眼前大大的「囍」字、散落一地的氣球,若無其事的回頭,給了我們一眼,那眼神似乎在說:原來這就是,最好的日子啊?
但沒經歷過,總談不上失落的滋味,好比洋洋的姊姊,讀北一女的婷婷,望著大廈對面,辛亥路橋底下親吻的戀人,看到出神的忘了自己才該面對的責任:一包垃圾,間接讓替她善後的婆婆,失足昏迷;為了一個吻,婷婷就此焦慮下去。
NJ的舊情人
然而最焦慮的不是別人,而是主角NJ。一如大多數的中年男子,壓抑、寡言,總是若有所思,但其實記性不好。連復刻版的NJ,兒子洋洋,都會因為吃到麥當勞而笑顏逐開;始終沒有笑容的NJ,在圓山大飯店電梯口巧遇舊情人時,連背影都沈重無比。
舊情人阿瑞,30年後風采依舊(柯素雲是女神!)。 巧的是,30年前的《青梅竹馬》裡,讓蔡琴心碎的情敵、侯孝賢的舊情人,也是柯素雲扮演。看看當時的氣質顏值,難怪站在電梯前面對著她的NJ只能背對著鏡頭陷入長思,始終不語。
當年的阿瑞,或者說如今的Sherry,像多數的中年女人,精明、世故,記性很好。念念不忘當年NJ的不告而別,即使逢場作戲的變臉技巧無與倫比,仍掩飾不了身為「受傷的女人」:火熱的心會變冷,而我依然那麼認真。阿瑞像是懸浮NJ頭上的思念,像那顆喜宴裡的粉紅氣球,想著想著就爆了。
洋洋與他的相機
而氣球之於洋洋,不是思念、不是保險套,就只是氣球而已。洋洋代表著純真的眼光,楊德昌說每個人都曾經是洋洋,只是在成長過程,逐漸一點一滴失去他。他還不懂得幻滅,也不懂得傾訴,所以對昏迷的婆婆,無話好說。
但洋洋懂得直觀,世界之於他,其實非常簡單。他學著透過相機觀看世界的模樣,讓我想到John Berger在《觀看的方式》寫過的:「我們只看見自己凝視的東西。『凝視』(gaze)是一種選擇的行為,我們關注的從來不只是事物本身,我們凝視的永遠是事物和我們之間的關係。」
這也解釋了,洋洋相機拍下那些看似「無意義」,或是主任揶揄「前衛藝術」的照片,那些模糊失焦、看不見的蚊子、那些後腦勺,拍得都是洋洋看見的事物本身,大人們急於找尋各種關係與意義,找不著或看不懂便氣急敗壞,防衛性的貶低其價值。洋洋聰明的多了,因為你看不到,我拍給你看,如此而已。像媽媽敏敏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,「事情其實沒那麼複雜啦!」
敏敏的困惑
身為洋洋的媽媽、NJ的太太,敏敏的存在感覺像是全天下媽媽的角色,只是陪襯。成為母親的另一面意義,就像失去自己的人生,忘了所為何事。也許敏敏的母親是面鏡子,讓她看到自己對於人生意義的困惑。活了大半輩子,努力了那麼久,最終也只能躺在那邊,啞然失語。
「怎麼那麼少?」敏敏哭著對自己的生命探問。
當日復一日的生活,吞噬掉人們的感知力,當人被時間訓練得麻木不仁,所能做的最好回應,大概就如同敏敏站在辦公室的影印機前,反射的光在她臉上反覆掃描,彷彿自己也被複印了,最後只能無關緊要的問一句:「結果是我有問題囉?」雖然敏敏的問題,可能連佛都度化不了。她選擇去山上閉關,才發現所謂修行的道場,其實不在人間,而在自己心中。
初心
不想麻煩神明的NJ,相信自己的初心。片中有段聲畫分離特別出彩,畫面上是肚裡嬰兒的超音波掃描,畫外音卻是日本客戶大田向NJ公司的簡報內容。聽到電玩遊戲的提案,卻看著跳動的新生命,人生與電玩,也許本質上真的沒什麼不同。
這幕戲我還注意到一個光影上的細節:大田簡報時,NJ的三個同事皆心不在焉,光線上因為投影片的播放,在他們身上反射,而顯得忽明忽暗;再下一個鏡頭,秘書把落地窗打開,窗外幾隻鴿子飛過,鏡頭跳到NJ身上,會議室恢復明亮,充足光線下的NJ望著簡報完的大田,露出認同的神情。在影像語言上,楊德昌已經暗示了他對這五個人的評價,三個同事只想便宜行事,NJ和大田則有著正直明亮的初心。
大田這個角色很特別,有著非典型日本人的從容,甚至有點禪意。鴿子會停在他的肩膀歇息(也許那隻鴿子也是NJ的隱喻?),做電腦的他談了一手好鋼琴,說話字字璣珠,還會「變魔術」,他幾乎是NJ對理想自我的投射!大田的初心埋藏著對當下的珍惜,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」這番言論,再再證明惺惺相惜的兩個中年男人,仍保有理想主義的光彩。
音樂裡的月光
當兩人坐在車內時,播放著貝利尼寫的歌劇《銀色的月光》,大田透露,音樂讓自己相信人生會是美好的。藉著共享對音樂的熱愛,NJ也因此敞開心房,說因為初戀,讓自己突然聽懂了從前聽不懂的音樂。
之後到鋼琴酒吧,大田忍不住獻藝,彈了日本國民神曲《昂首向前走》,又名「壽喜燒Sukiyaki」,最後還獨奏了貝多芬的《月光奏鳴曲》,也是這段音樂,讓NJ再次想起初戀情人阿瑞,致使他之後回到辦公室撥電話給她。
月光的意象,不斷出現在配樂中,或許阿瑞就是NJ的月亮,皎潔明亮,遠遠發光。NJ回到辦公室撥打越洋電話給阿瑞時,楊德昌刻意讓整間公司漆黑無光,鏡頭中隱約可見遠景有微弱光源之外,側身坐在近景的NJ,不見臉上表情,在黑暗中說的心底話,才特別真誠動人。
折射之光
楊德昌視布列松為偶像,兩人的影像質地有不少相似之處:理性、精密、冷調,好似喜讀哲學的外科醫師或工程師,講究鏡頭排列的內外在邏輯,又不失哲學宗教意味。好比布列松認為「一個聲音能取代一個影像時,刪除那影像或抵銷其作用。 耳朵更走向內,眼睛更走向外。」以上那個NJ在漆黑辦公室講越洋電話的場景,完全體現布列松的電影精神!
說到影像語言,《一一》裏頭有著許多精密構圖的鏡頭,以及聲畫安排,有些初次看即讓我震撼不已,有些是反覆觀看後才漸漸領略其滋味,甚至這次在大螢幕看,才發現的細節。
精心安排的折射鏡像,大量被使用在片中,好比敏敏在漆黑辦公室往窗外看,鏡頭拍窗上的敏敏反射倒影,窗外不段閃爍的紅燈號誌,恰恰好被構圖在敏敏心臟的位置,閃爍的燈,同時也是跳動的心,夜幕低垂後的冷清街景,整個城市的脈動,呼應敏敏內心的疏離。
例如婆婆被送急診後,NJ與阿弟趕到醫院,鏡頭拍著鏡面玻璃,窗框把NJ與阿弟各自隔開,左邊的遠景有美國跟戴立忍等友人在醉後歡鬧,三個區塊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情。細心一點的話,還會發現NJ與阿弟腳邊地板,有小小貼著幫助走位的記號,也算是觀影的另類樂趣。還有阿弟透過玻璃,看著自己的新生兒,玻璃反射阿弟的倒影,他不斷對嬰兒逗笑,那模樣看似是在自嘲一般。
凝視
全片最出彩的角色凝視之一,必定不能忘了洋洋的性啟蒙場景!他走進視聽教室時,暱稱「小老婆」的女孩隨後進來,投影幕正在播放自然科學的教學影片,講述生命的起源於閃電,當天雷勾動地火,電光交加,「小老婆」走到螢幕前方,她的剪影被背光閃電烘托,下一個鏡頭跳到洋洋的凝視神情,旁白說著「那是一切的開始」。
接著雷雨聲延續,過渡到下一個場景,洋洋的姊姊撐著雨傘站在路邊,與胖子隔街相對凝視。剪接與音效上的細節,在戲院觀賞時更加立體有層次,不得不佩服楊德昌創作思慮之縝密。
凝視鏡頭還包括一系列眾人與婆婆說話的場景,鏡頭都是一動不動的沈穩,宛如神明聽願的不動聲色。其中阿弟的支吾其詞、婷婷的內疚自責,以及NJ的有感而發,都如鏡像般投射出角色的內在世界。楊德昌在解說裡透露,要拍NJ對婆婆獨白那場戲之前,吳念真請求要先抽根菸,於是楊德昌讓他在陽台上抽了一根菸,回房間拍攝時,便一次就OK,沒有NG重拍。楊德昌不斷稱讚吳念真是台灣最好的天才演員。
初吻
我印象最深的凝視,是個長鏡頭。也就是婷婷與胖子的初吻!辛亥路與泰順街口的陸橋底下,是婷婷、莉莉與胖子三角習題的主場景,片中NJ家的公寓羅曼羅蘭大廈就在旁邊,對於缺乏私人空間談情的高中生來說,陸橋底下是個稍微有一點點隱私的公共場所。
而婷婷與胖子看完演奏會(該場景彈鋼琴的是楊德昌,夫人彭鎧立拉大提琴),兩人在陸橋下接吻的廣角鏡頭拍了很多次,因為楊德昌要精準控制紅綠燈的轉換時機!
仔細看會發現,胖子說服婷婷時,交通號誌是紅燈,他告白「我的心裡,只有你」之後,燈號瞬間變成綠燈,當婷婷遲疑不決時,綠燈開始閃爍,變成黃燈之際,胖子吻了婷婷,霎時變成紅燈了!男女之間情意的一攻一守,危險挑逗與理性自持的邊界,在簡單的號誌燈號指引下,竟然交錯著前所未有的秩序與失序感。楊德昌彷彿化身指揮家,電影手法精確成熟不已。
年輕的日子
除了強烈的理性邏輯,《一一》也有柔情似水,如詩寫意的一面。個人最喜歡的段落是NJ去東京過的那段「年輕的日子」,彭鎧立彈的鋼琴獨奏曲《One More Moon》,伴隨著NJ在計程車內望外看到的東京辦公大樓,燈火通明,頓生寂寥,跟我首次去東京乘坐利木津巴士看到的景象如出一徹,東京真是寂寞的城市!
寂寞的東京,卻是NJ與阿瑞關於初戀的鄉愁。如同大田對阿瑞說的,你是他的音樂(his music..),相對於女兒婷婷那一代的美式約會:NY Bagel、好萊塢電影;NJ與阿瑞年輕時候的約會要日式得多:鐵道、平交道。時代記憶的變遷,也悄悄鑲嵌在電影背景。九點的台北,十點的東京,兩對不同時代的戀人,現實與記憶,交叉剪接在此時此刻之中,我想起許美靜唱的《都是夜歸人》:「我們/於是流浪這座夜底城市/徬徨著徬徨/迷惘著迷惘/選擇在月光下被遺忘」。
兩人並肩散步,漫遊城市,在神社解開多年情仇,到被時光凝結的熱海,過了懷舊的一晚。楊德昌對東京和舊情人,有著莫名的眷戀,在《青梅竹馬》裡,蔡琴問侯孝賢這次有沒有去東京?原本已經離開的侯孝賢,回過頭出現在房門口,淡淡的說了句:「只是路過,沒有停留。」看似在對旅程的問答,實則是戀人對信任的試煉。在楊德昌的電影中,東京等於初戀,等於舊情人,永遠只能路過。
於是NJ和阿瑞從熱海回到東京後,在旅館門前互道晚安後,阿瑞已掩上的房門,在NJ再次輕聲呼喚後打開,此時阿瑞的神情充滿期待,而NJ最深情的時候總是背對著鏡頭,他淡淡且篤定的表白:「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。」那時那刻,昔日戀人的愛,在東京,永遠停留了。
告別
婆婆還是走了。原本不願意跟婆婆說話的洋洋,像是瞬間理解了甚麼,回到房間振筆疾書。告別式場景的選擇,楊德昌解釋過,為何挑選有別於一般傳統的祭祀場所,他覺得婆婆生前是老師,於是在校舍佈置一個簡單的告別式,更能體現影片的簡單精神。
洋洋的致詞,堪稱影史經典的獨白,把楊德昌的心聲用最純真的語調說出,從一個孩童口中說出「我也老了」,足見創作者仍舊對世界充滿深情,然而成長是幻滅的開始,洋洋代表著每個人的純真,在與世界發生關係之後,也只得一點一點老去;青春很短,等待長大的時間卻很長。
還記得楊德昌接受法國媒體訪問時,記者問他一個對所有創作者來說,幾乎是永恆而難解的問題:「Pourquoi filmez-vous? 為什麼拍電影?」,不像大多數導演可以口沫橫飛大談創作理念,只記得楊德昌的答案跟問題一樣簡單。
「這樣我就不需要說那麼多話了。」
看了無數遍《一一》之後,真的能體會到他說的,電影讓生命延長了至少三倍!不過我覺得,楊德昌其實沒有魔法,跟大田一樣,他只是記得所有的牌而已。